赵宝昌,原大连医科大学副校长,生化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现任基础医学院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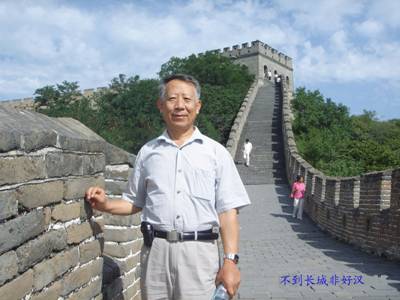
1958年我有幸考入大连医学院这所位于黄海之滨的医学殿堂。除了1963年到1967年在山东医学院做过四年生物化学研究生外,一直生活和工作在这里。大医为我提供了展示自己的平台,为人民服务的场地。我在这里成长、在这里耕耘。时间如梭,弹指一挥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大医的风风雨雨已经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深深的感到,大医有一种精神,一种不可战胜的精神。这种精神之力量无比强大,只要来到大医学习和工作,你就会耳濡目染,为这种精神所感染,为这种精神所驱动。
大连医科大学不是清王朝开办的洋学堂,没有百年苍桑;也不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外国人在华设立的大学,没有教会色彩。大连医科大学的前身先后是关东医学院、大连大学医学院和大连医学院,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支援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利用当时大连的特殊政治、经济和地理环境,于1947年5月4日创建的第一所正规医科大学。正如中共旅大市委于1949年给大连大学制定的办学方针所说,这所学校是“人民的正规大学”。它遵循“科学与政治结合、为人民服务、和人民打成一片”的精神。这一指导思想奠定了大医的发展方向,确立了大医人的办学理念。大医人正是在这一指导思想的指引下,树立了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的解放、无私奉献、艰苦奋斗、不屈不挠、顽强拼搏、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和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种为了革命事业而百折不挠的精神就是大医的校魂。这种精神一代接着一代,不断被传承,不断被发扬光大,不断被刷新。
大医在建校的短短几年间,在党的领导下,广纳百川,吸引了大批海内外进步的专家教授。他们来到解放了的大连,为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祖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魏曦教授在抗美援朝时期参加了中央卫生部组织的美国细菌战调查团,在枪林弹雨中搜集美国细菌战的证据,向全世界揭露了美国侵略者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获得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并于1956年最高国务会议期间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宴请,与毛主席并肩而坐。吴襄教授编写了全国第一部生理学教科书。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医拥有3位一级教授,6位二级教授,从这里走出了10位院士,为卫生部举办了12期师资培训班。那时的大医就已经跻身于全国高等医学院校的先进行列。
虽然在反右扩大化的1958年,有数以百计的师生员工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了严酷的精神打击,但他们正是由于有着大医的这种精神,拳拳赤子之心,无怨无悔,在逆境中仍然默默地为党工作,为人民的健康事业辛勤的奉献着。他们创业、进取、勤奋、团结、爱校。1963年东北和华北地区暴发数十万例“未明热”,刚刚摘掉右派帽子,尚未完全恢复职务的乔树民教授,冒着重大政治风险,力排众议,挨家逐户进行调查,阐明了钩体病的病原性质、传染源、传播途径和防治方法,有效地防止了该病的蔓延。归国华侨,1953级潘恩良同学于1958年毕业前夕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在台安地区,含冤多年,对党对人民一片赤子之心始终不减。为了解除人民的病痛,他忍辱负重,勤勤恳恳,日夜操劳,鞠躬尽瘁。1960年,他虽每月只有27元的生活费,身患浮肿仍坚持手术,多次为抢救病人献血,和台安人民共度困难。他对医疗技术精益求精,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表现出党哺育的大医学子的高尚品质。他被卫生部授予“人民好医生”的光荣称号。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医院被命名为“恩良医院”。
我一迈入大医的校门,老一代大医人造就的这种革命精神的春风就扑面而来。迎新老师的热情接待,同学之间的亲切关怀,授课老师到学生宿舍问寒问暖,都给了我一片温馨,一份感动,一种激励。班级党组长大姐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增添了我对共产党员的崇敬和对党的热爱与信赖。在党的阳光照耀下,我很快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从此我就开始自觉地接受党的教育和考验,并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的事业。在大学期间,我们经历了全民大炼钢铁、深翻地、抗旱、向党交心、教育革命等一系列运动。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校33%的师生由于营养不良而患上浮肿病和闭经。学生食堂的包米面“水肿”饼子中夹着柞树叶子,又涩又苦,菜是没有油水的海带片。但全校师生毫无怨言,教学科研活动一切如常。为了度过难关,我和我的同学在大连市委党校经过简单培训,到新金县指导人民公社社员大搞代食品。在严寒的冬天,我们与人民公社社员一道,每天只吃3两粮。虽然我们很多人的浮肿加重了,但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都胜利地完成了市政府和学校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1960年,为了满足辽宁省高等医学教育快速发展的师资需要,省政府决定由沈阳医学院和大连医学院各办四个专业师资班。我们五八级80名同学都坚决地响应了党的召唤,被抽调到药理学、生物化学、微生物与寄生虫学、生物学等四个专业班。这是党的安排,大家都高兴地来到了专业班,我们刻苦学习业务,积极参加劳动,立志成为一名优秀的基础课教师。1963年国家出于反修防修的需要,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接班人和高层次的业务人才,开始在全国正规招收研究生。年级党总支书记召开年级大会,动员、号召同学们积极响应党的召唤,报考研究生。我积极地报了名,经过半个月的脱产准备,成功地考取了山东医学院生物化学专业研究生。
大医是历经磨难的学校。为落实党中央的“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支援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大医于1969年春被整体搬迁到贵州省遵义市,组建遵义医学院。全校师生都毫不例外地听从了党的安排,仅用80天就把教研室的全部仪器设备,甚至每一个试管,每一张组织切片都仔细地包装好,整整装了100多节火车皮,安全运抵遵义。每个家庭的私人用品也只在几天的时间内包装完毕,一声令下,运到富国街原大连油漆厂的露天货场等待装车。老天似乎有意与我们作对,或许也在有意磨练我们,所有的行李、木箱均被夜间的一场倾盆大雨淋湿。到达遵义后,很多家的被褥、书籍长了霉,黄豆生出了豆芽。广大师生不顾水土不服带来的严重腹泻,全力投入到学校的建设中去。在自来水管道没有接通的情况下,附属医院的医护人员用脸盆从几里外的山村端水,保证了这所在贵州闻名遐迩的医院在一个月内正式开诊。同时,医院还组建了多个医疗小分队下乡巡回医疗。我和许多老师一起,自己的小家还没有整理好,就带领从大连带去的六四、六五级学生下乡进行复课闹革命和巡回医疗。
为了迎接1972年的招生工作,在校革命委员会的安排下,我带领由前后期各科老师、医生、检验师、护士、干部组成的一支二十余人的“教育革命实践队”徒步拉练到百余公里外的湄潭县黄家坝区。在乡下八个月,我们以当时特有的方式,一面为贫下中农看病,培训赤脚医生,一面进行师资队伍的自我锻炼。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利用耳根麻醉法治愈破伤风病人,用当地的草药治愈大叶性肺炎病人。用“一根针、一把草”为广大农民解除病痛。自己刻印讲义,举办赤脚医生培训班。1971年秋,学校组成教材连,我任连长。大家很快编写出教材大纲,并下乡征求贫下中农意见。在农村,我们虽然没有听到贫下中农对教材大纲具体内容的修改意见,但他们热切地希望我们能为农村培养出他们真正需要的“一把抓医生”。我们把它作为编写教材的指导思想,在全校各教研室老师的共同努力下,仅三个月我们就编写出工农兵学员学习用的基础与临床课的全套教材。为第二年新生入学做好了准备。1972年遵义医学院迎来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
说也奇怪,不知何因,内迁到遵义的师生员工几乎都先后得了一些“怪病”。1972年开始,“神经根炎”、肝脾肿大,以及后来的恶性肿瘤等疾病陆续严重地折磨着,威胁着,也严峻地考验着这批工作与生活在遵义医学院的大医人。“神经根炎”来势凶猛,其临床症状多种多样。轻的表现出肌肉不自主的跳动(肌跳)、心率过速或心率过缓或心律不齐,心电图显示束支传导阻滞。重者昏迷、肢体僵硬不能活动、癫痫样抽疯、自主呼吸停止等等。全校人员几乎无一幸免,自主呼吸停止者需要“捏皮球”(人工呼吸)进行抢救。肝肿大达肋下5公分、剑突下9公分、脾肋下3公分的师生员工不计其数。附属医院一度因需要住院抢救的本校职工过多,不得不对外停诊。校领导去贵阳汇报工作途中遇上车祸,在校工作多年的司机师傅遇难,几位领导受伤,人人悲痛欲绝。但大医人却没有被这些病魔和不幸所吓倒,他们擦干眼泪,继续顽强地与疾病和困难斗争着。一人有病大家帮助,一人住院大家轮班守护,相互照料,表现出同志与亲人般的深切革命情谊。全校职工只要能走得动,就坚持到校上班、上课。全校的各项工作都有条不紊地正常运转。经全校人员千方百计地共同奋斗,疫情有所缓和。大医人排着整齐的队伍,穿着崭新的衣服,迈着矫健的步伐,高举国旗和校旗,校军乐队高奏“歌唱祖国”、“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沿着遵义市十里长街健步游行到遵义会议会址,以示“重振军威”,受到遵义市人民的夹道欢迎和祝贺。这就是大医人的自强不息、奋力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这就是大医的校魂。疾病没有侵蚀掉大医人忘我工作的无私奉献精神。遵义医学院一批批学生入学,又一批批学生毕业走向社会,一批批科研成果问世,一批批先进模范涌现。1978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贵州省高等医学院校共有六项成果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其中遵义医学院就占了5项半。
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大连医学院在大连市原址复建。这是大医人的第三次建校,这次建校的困难之巨大,不亚于1947年和1969年那两次。在复建初期,没有校舍,没有仪器设备,没有足够的师资,一切都需从零开始。大医人还是满怀艰苦创业的豪情和战胜困难的斗志,创造出了一个个不平凡的业绩。无论是利用五四路200平方米的托儿所办学,还是利用附属医院的安波分院,以及租用210医院地下室做实验,无不体现出大医人的钢铁意志和聪明才智。复建的首批1978级106名同学,十分理解学校的处境,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安心学习,用知识武装自己。他们在1983年8月卫生部组织的44所高等医学院校的医学专业毕业生业务统考中,以平均84.5分(全国平均82.63分)的优异成绩,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被卫生部列为考试成绩的第一档次。第二年,1979级再次参加全国毕业生统考,平均分数进入前三名。这一情一景,一人一事,都是大医人的骄傲,都是大医校魂的展现。
大医人的这种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的解放、无私奉献、永往直前、永不言败的革命校魂,使得大医人能像白求恩同志那样,表现出“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锤炼出大医特有的校风:团结、严谨、求实、创新。培育出大医人的高尚教风:重教、严教、善教;造就了大医学子的优良学风:志学、致学、治学。我坚信,在当前社会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大医人一定能不辱使命,站的稳,走的直,大医精神永远不倒。大医人犹如荷花,它“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愿大连医科大学永葆青春,像一株高崇入云的青松,不怕风吹雨打,不畏地冻天寒,永远挺立在世界医学之巅。
祝大医精神如旭日东升,永远辉煌!